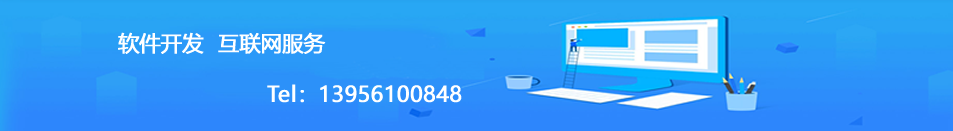雍正五年,当雍正处理好继位之初的紧张大案后,将曾作为雍正早年最心腹的门下戴铎被以朋党罪名处死,尽管戴铎最多算个中层官吏,由于身份和经历特殊,一时之间引发广泛关注。
这个曾经努力钻营并不断给雍正出点子的奴才没想到主子当了皇帝未能给他的顶戴再进一步,而是将他项上人头砍下。
对于戴铎的处死,应该延伸到康熙时期诸皇子的事件当中。
康熙的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在其兄弟们为争夺储君发生激烈冲突时,他摆出一副俨然事不关己的超然状态,除了与宗教人物密切往来外,还编纂了《悦心集》,胤禛所作一切就是告诉当时所有人,我对皇位不感兴趣。
然而这只是一个烟|雾|弹,他的门下奴才戴铎替他到处收集消息,并出谋划策,而这个门下走狗的却不断招摇和膨胀索取越来越让雍亲王感到不安和反感。
戴铎在雍正眼里与后来被其重用的臣下不同,在当初使用他是因为无人可用,瞧不起他又不得不依靠他通报消息。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开始,戴铎作为雍亲王的门下唯一心腹主动为胤禛献计献策劝他积极参与储位竞争:
“当次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
并洋洋洒洒写下千言,替雍亲王分析当前形势和需要如何主动进攻,前后为雍正量身定制提出“三策”,以求在日后谋夺储位进行发力。
此前雍亲王帮助戴铎外放福建知府后,戴铎在给他的信里还说:
“在武夷山,见到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等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禛收到信后非常感兴趣,在信后迫不及待追问:
“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文献丛编》
戴铎收信后可谓吊足了雍亲王胤禛的胃口,在回信中说:
“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
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
”胤禛无奈,用了羡慕口吻回他说:“你得遇此等人,你好造化。”
雍亲王对其书信只推说“与我分中无用”、“皇帝乃大苦之事”。
此时的雍亲王对其既厌恶又不能不依靠其在外面搜集信息,却从不敢叫其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
甚至在雍正三年的时候,雍正给年羹尧的密旨中说:
“戴铎乃朕府邸旧人,行止妄乱,钻营不堪,暗入党羽,造捏无影之谈,煽惑众听,坏朕名声,怨望讥议,非止一端,朕隐忍多年,及登大宝,乃知此人无父无君之辈,宽其诛而皆弃之不用。”
可见戴铎在当时的招摇让谨慎的雍正十分恐惧和愤恨,又无可奈何。
那么戴铎的“三策”是哪三个方面呢?第一就是劝胤禛决不做旁观者。
第二要吸取废太子的教训,不可凌辱兄弟,对诸位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第三,要把雍亲王邸的人外放出任要职,为将来储备人才,即“加意作养,始终裁培”,“使本门人由小而大,在外为督抚提振,在内为阁部九卿”。
对这三点来说,戴铎说出了一些要点,但是也暴漏了他的私心,由此在日后遭到雍正嫉恨厌恶。
即不断要求雍正给他找好地方外放,到了当地又不安心,屡次提出各种要求。
尽管用满足了他对外放的要求,但是一到福建,戴铎就向雍正大吐苦水,说自己在福建如何水土不服,想让雍亲王想办法把他弄回北京:
“奴才自问愚昧,功名之志甚淡,兼之福建水土不服,染病至今,特启主子,意欲将来告病,以图回京也。”
四阿哥胤禛收信后也给他一个大套路说:
“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
此后戴铎多次向胤禛苦求回京,胤禛越发反感他,生怕他招摇出什么事来。
在康熙五十六年时,戴铎给雍亲王继续写信表示“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雍亲王非常不耐烦回信道:
“天下无情无礼,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
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几个月后,当听到康熙决定在诸阿哥人中选拔太子时,戴铎又给胤禛写信提出了新的要求说“台远在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调到那里,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言外之意就是四阿哥肯定不能成功被选为太子,他去台替胤禛打前站,俨然把胤禛往“造**”上的道领。
胤禛接到信后,气得不知如何痛骂:
“你在京若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
戴铎俨然成了雍亲王“猪一样的队友”。
但是此刻雍亲王胤禛在外边可以通风的只有这一个人,又不得不用,不得不对其敷衍搪塞,面对戴铎喋喋不休的大嘴巴,四阿哥也只能听之任之。
戴铎依旧屡表忠心。在此后又给雍亲王胤禛写信说:
“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
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之惊心,特于彼处探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
奴才密向彼云:
‘八王懦弱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
戴铎这种主动向康熙身旁机密要臣打探消息,在政治家庭长大的胤禛完全知道戴铎信口胡言,忽悠自己罢了,以大学士李光地的政治韬略完全不可能对其表露任何真实观点,更何况戴铎的官阶见不见得到李光地还是另一回事。
胤禛在回信中再次将其痛骂:
“你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
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可见雍亲王胤禛对其厌恶而又无可奈何戴铎这块狗皮膏药。
戴铎在一年后给胤禛寄来几样扇子后,胤禛还是冷淡而处处警告他说:
“你自家看看你的扇子和你的启帖,你是什么不知道我的。放着你,你以后四次具折请安。”
在康熙六十年,胤禛将其调往四川任布政使,在其上任前夕,胤禛对他再次警告说:
“你此去当时时勉励,惟以治心为要,心一正,则天地神明自必加佑。”
这种明示已经说明,在胤禛心里,戴铎属于小人之类的不正经人,处处歪门心思,格局和手法又不够大不够高,根本不配成为其真正下手。
此后戴铎调往四川担任布政使,其兄等人也是由胤禛出面活动安排到河南,胤禛虽然生气此刻却也无可奈何,打发远远的,不失一时之策。
果不其然,当胤禛继位后成了皇帝,没多久,就命令年羹尧其以朋党之罪处死。
如果仅仅以灭口戴铎,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戴铎的层次最多是一个能在外面打探到一点难正真伪的消息的狗腿子,对当时的胤禛帮助并不大,与直隶总督李绂受命负责处死八阿哥的机密程度更不在一个层次,戴铎的作为却因此让雍正不断厌恶其小人嘴脸和其到处煽风点火。
虽然是自己的手下人,戴铎却一直被其厌恶,当了皇帝后,为了不让其继续添乱,顺路将其纳入朋党处死,以解昔年厌恶而又抛不掉的憎恶。